“飯黨”和“面黨”現已呈現了
“人類飲食結構和內容是逐步豐厚和完善起來的,演進的過程并沒那么劇烈。秦朝時間較短,很難全部反映秦漢期間的飲食文明。放眼這以后跨過400年的漢朝才更全部和客觀。”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劉尊志說。
到了漢代,稻、黍、稷、麥、菽這五谷現已很遍及了。盡管,黃淮及以北地區的大家以黍、稷、麥為主食,而南邊和西南地區的大家則以稻米為主。
劉尊志以為,在西漢,跟著杵臼、碓、磨等糧食加工技術的開展,谷物粉面制成的主食,現已改變了大家曾經食用干飯和粥的習慣。這么看起來,“飯黨”和“面黨”之爭還真是源遠流長。
在漢代,面食的做法十分多樣:用水煮稱為“湯餅”,用籠蒸稱為“蒸餅”,用火烤的稱為“爐餅”。其間,“湯餅”有豚皮餅、細環餅、截餅、雞鴨子餅、煮餅等;“蒸餅”有白餅、蝎餅等;“爐餅”有燒餅、胡餅、髓餅等。
相比谷物直接煮飯、熬粥,漢代公民在面食上的創造性顯著更高。比方,上面說的胡餅,即是在餅上撒上芝麻再烤,髓餅則是用動物油脂作為作料,和在面里,顯著風味更佳,養分也更豐厚。
此外,其時的大家現已能夠蒸制饅頭、制造包餡的面食了。在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的竹籠里還盛著米糕。
可是,“飯黨”也有不少挑選:不只有麻、蕎麥、青稞、小豆等傳統作物,還有像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綠豆、胡麻、鵲紋芝麻等外來品種。
吃著小火鍋還能涮豆腐
在西漢期間,一種青銅染爐十分流行,以至于在許多地方都有出土。這種染爐分為三個結構:主體為炭爐,下部是接受炭灰的盤體,上面放置一具活動的杯。它曾讓幾代專家對它的用途疑惑不解,直到今天,考古界才斷定它即是一種相似現代意義上的“小火鍋”。
聞名考古學家王仁湘曾撰文以為,染爐是漢代前后貴族飲食日子的一個旁邊面,是一種高雅的食器。由于漢代實行的是分餐制,一人一案,一人一爐,甚是愜意。這一幕也被記錄在漢代畫像石上。
在這種場合下,酒簡直是不行缺少的助興之物。從1968年河北保定市滿城漢墓的出土文物能夠看到,方形大陶缸上還寫著酒的稱號、品種和分量,如“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
在江西海昏侯墓、西安張家堡新莽墓葬都出土了一種相似蒸餾酒器物。精巧的器物讓人不只“腦洞”大開:蒸餾出的酒水傾入金樽,度數更高,口味也愈加甘洌,直讓人耳酣目熱。
提到火鍋,不能不提我國人涮火鍋的“標配”——豆腐。這一國民食物傳說起源于西漢淮南王劉安在八公山煉丹時的“無心插柳”。由于美味又便宜,它逐步在民間流行起來。在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墓東耳室南壁的畫像中,一些專家以為,其間正描寫了民間制造豆腐的場景。
那時的食材比如今還豐厚
漢人嗜烤肉,在畫像石上也看得明明白白。在山東諸城前涼臺村發現的一處庖廚畫像石上,刻畫了一幅跟如今相差無幾的“擼串兒”場景:一人串肉;一人打著扇子,翻轉肉串;別的兩人跪立在爐前等著。
那時的食材,比起如今還豐厚。畫像石上,不只顯現了宰牛、羊、豬及殺雞、屠狗等情形,還懸掛著龜、魚、雁、鳥、兔等不一樣動物的腿肉。同時,他們也會捕食一些野生動物來改進飲食結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從漢代的打獵圖和出土的動物骨骼不難看出,傳統“野味”就有鹿、麋、野豬、兔、雁、雉、雀、鶴等,像熊、虎、豹、狼這么的猛獸也不在話下。在徐州翠屏山西漢墓中,還發現了魚骨、魚子和螃蟹等。看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必定比這還早!
哪種調味品最好吃?劉尊志建議試一試“魯豉”,“這是漢代較為知名的品牌商品,據史料記載,還有人由于賣豆豉成了富翁。”
除此之外,咱們如今煮飯常用到的花椒、姜、蔥、桂皮、茴香也被漢朝人使用了。在它們的協助下,肉的滋味愈加豐厚,能夠做成火腿、肉脯和肉醬。
香菜和蔥現已發揮了實力
關于許多人來說,香菜這種逆天的存在,是怎樣來的呢?答案是,外來的。在漢代,香菜和蔥現已發揮了實力,不再是蔬菜,而是一種首要的調味品。
漢人吃的蔬菜,整體來看,有根莖類、莖葉類、蔥蒜類、瓜果類等。聯系史料記載和一些考古實據,能夠肯定的有筍、藕、葵、芥菜、韭菜、蕹菜、蕪菁、薺菜、芋頭、葫蘆、荸薺等。黃瓜也是那時從西域傳入的。
在生果方面,考古學家發現,在漢代,我國原產的生果就有桃、梨、棗、酸棗、杏、李、柿、梅、楊梅、青楊梅、廣東含笑栗、枇杷、橘子、柑橘、柚、荔枝、桑椹、銀杏、松子及香瓜、甜瓜、菱角等之多。
在漢代,最有名的外來生果即是葡萄了,它也在西漢期間的墓葬中被發現過。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石榴、橄欖現已傳入我國,并開端被培養。絲綢之路構成后,胡桃(核桃)、無花果、番木瓜、胡瓜等隨之而來。
不過,也有一個“懸案”。在甘肅涇川出土的漢墓里,有一個陶灶上雕著有蘿卜,可是考古學家并沒有找到蘿卜在秦漢三國期間的更多依據。
這個孤單的蘿卜,不會是“穿越”回去的“吃貨”悄悄畫上去的吧?
我國人5000年前就會釀啤酒
據新華社電 中美研討人員23日報告說,他們在西安市米家崖遺址發現了5000年前釀制啤酒的依據,這是迄今在我國發現的最早釀酒依據,闡明我國古人可能早在5000年前就開端享受喝啤酒的趣味。
這項研討宣布在新一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負責該項研討的斯坦福大學考古專業博士生王佳靜說,如今的啤酒大多是由大麥或小麥等質料釀制而成,而他們發現的啤酒質料由黍、大麥、薏米和少數根莖作物混合而成,其間大麥不是我國本鄉培育培養的,是由西亞馴化成培養種后傳入我國,別的質料均在我國上古期間就有。
陜西省考古研討院邢福來是這次發掘工作的領隊,斯坦福大學東亞言語與文明系教授劉莉與美國楊百翰大學教授特·巴爾參加研討。他們在米家崖的兩個窖穴里發現了與制酒有關的器物,包含闊口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可移動的灶,時代測定為介于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經過殘留物的科學分析,從中找到了啤酒釀制的三個依據。
王佳靜說,“一些大規模的仰韶晚期遺址有顯著的社會階級化特色。咱們發現的酒可能是其時社會一些高層人士用于宴饗活動、宗教儀式的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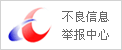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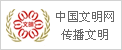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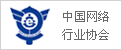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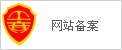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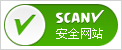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3-2022 Brand food.c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3-2022 Brand food.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