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全球疫情拐點還沒來到,疫情結束還遙遙無期,但不可否認,隨著新冠疫苗在全球的迅速普及,特別是中美兩個世界主要經濟體有望在今年之內形成免疫屏障,因此,全球疫情形勢正在向著日益受控的方向發展,即使有些國家和地區疫情出現反復,但卻不會影響到全球疫情防控大局,更不大可能改變全球經濟大反彈的格局。
有鑒于此,我們看到,那些新冠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國家和地區正在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布局后疫情時代的經濟振興、復蘇與發展。香港作為全球經濟的一分子,在過去的近一年半時間里,深受疫情之苦,經濟遭受重創,如今,更是得為后疫情時代早作謀劃,全面布局。
防控疫情不松懈,接種疫苗快推進
日前,港府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香港經濟增長數據,同比去年第一季度明顯回升了7.8%,環比去年第四季度也上升了5.3%。情況雖然好于預期,但不能不看到,香港的經濟復蘇十分不全面,甚至可以用殘缺不全來形容:首先,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經濟的回升主要動因來自于內地和美國經濟回升而引致的貨物貿易的進出口大幅增加,香港從中受惠,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經濟增長動能仍在衰減,譬如,香港的消費市場,一方面,香港超過四成市民的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也就是說,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收入沒有增加甚至下降;另一方面,十分依賴境外游客消費的香港今年五一黃金周期間只接待了不到一百位內地游客,海外到港人數也只有二千多人。顯然,香港消費市場仍然處于萎縮之中。再如,去年港府應對新冠疫情以及推出的保就業、保民生計劃已經消耗了近四千億的財政儲備,今年疫情持續,勢必繼續消耗財政儲備,而且為了應付不時之需,特區政府手中還必須掌握足夠的資金。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財政儲備其實已經十分有限,試圖寄望港府推出大規模基建計劃以刺激經濟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總之,香港經濟復蘇前景不容樂觀。
香港要吸取去年核酸檢測的教訓,對市民的疫苗接種提出明確要求,并且采取督促措施。
不久前,特首林鄭月娥在參加海南博鰲論壇時預期,2021年香港經濟有望實現3%至5%的增長。由于2020年香港經濟出現了6.1%的負增長,因此,即使香港經濟今年實現5%的正增長,那么,2021年香港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環顧全球,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皆出現明顯反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6日的最新預測,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將增長將達到6%,中國經濟將增長8.4%,美國增長6.4%,歐元區增長4.4%,日本增長3.3%,顯然,如果香港經濟今年只出現了3%的反彈,那么,香港經濟恢復與表現不僅趕不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有可能落后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表現。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香港經濟2021年難有大起色幾乎成為定局。因為,直至現在,香港的疫情仍然沒完沒了,雖然疫情沒有再次出現大爆發,但是始終不能夠根除傳播鏈,特別是變異病毒已經進入香港,又令香港的防疫形勢出現新的變量。如此,香港只能將自己隔絕于世界之外成為孤島。也就是說,今年大部分時間里香港仍然無法從外部獲取足夠的經濟資源與發展動力。這正是香港經濟今年無法樂觀的要害所在。
香港在防疫工作上一開始把防疫重點對準內地而疏于對海外往來人員的管控,姑且不論此舉是否正確,但當內地已經迅速控制住疫情而海外疫情愈演愈烈之時,香港仍然沒有及時作出調整,結果導致該防的沒防住,不該防的卻花重兵把守,不僅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而且結果令人失望。
雖然現在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已經在全球迅速推開,但香港的接種工作卻裹足不前,盡管特區政府提出要采取誘導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但可以預期,在所謂的自愿接種原則背景下,香港的疫苗接種工作也將像去年展開的自愿核酸檢測活動那樣,接種人數只會占到七百萬港人中的一小部分。如此一來,2021年香港的疫情仍然會尾大不掉,即使香港希望撤銷管制措施與外界重新往來,但在新的變種病毒的威脅之下,沒有那個國家和地區敢敞開大門與香港自由往來。那種認為香港疫情不必清零便可與內地實現通關的想法和建議,不僅是天真的,而且是自私的。
香港當務之急仍然是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香港本來有一手好牌,但卻打出了一個差強人意的結果,香港的優勢正在一個一個消失,而且內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機遇也一個一個被錯過,尤其去年以來疫情防控工作的不佳表現更是令香港經濟掉入深淵,可謂遺害無窮。香港當務之急仍然是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能夠疫情稍有好轉就放開管控措施,然后一旦疫情爆發又急匆匆收緊管控,令香港的疫情防控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與此同時,要吸取去年核酸檢測的教訓,對市民的疫苗接種提出明確要求,并且采取督促措施。只有如此,香港經濟才有希望擺脫疫情困擾,出現真正的實質性轉變。
積極主動融入大灣區一體化發展格局
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一種錯誤的認識,那就是香港只要緊跟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后面跑就能發達無憂,然而,最近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表明,歐美日等所謂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大不如前,尤其是歐美日相繼陷入經濟危機、債務危機、金融危機不可自拔,而且還給香港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到2000年的科網泡沫爆破,從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嘯到2009年開始的歐債危機,每一次都給香港帶來不同程度的破壞和拖累,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及時出手相助并得到國家諸多的支持和幫助,香港有可能已經沉淪下去。香港試圖跟隨歐美日的后面實現發達夢,這條路已經越走越窄,走不下去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全世界都在搶搭內地發展的快車,只有搭上國家發展這趟快車,才是香港實現持續繁榮和新的大發展的根本出路,而要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就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戰略格局當中。
香港只有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并以此融入到國家發展的大局之中,才能破解香港所面臨的系列困境和難題。
2020年10月21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駱惠寧指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的事業發展是香港不可錯失的重大歷史機遇,機不可失;他強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能等、亦等不起;他特別呼吁,不能讓“歷史性機遇”成為“歷史性遺憾”。駱惠寧的重要講話對香港社會來說無異于警港醒言,對香港社會各界能夠起到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作用。
不能不承認,同樣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較之澳門,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趕搭內地發展快車,抓住中國發展機遇等方面可謂差強人意,也正是因為如此,澳門回歸之后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人均GDP由回歸時1999年不及香港一半的1.5萬美元快速倍增至2019年的8.5萬美元,約為香港的兩倍。相形之下,香港的發展步履蹣跚,像老牛拉破車。特別是2019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發生的社會動亂以及去年爆發新冠疫情的沖擊,更令香港經濟遭受沉重打擊。
雖然2020年7月份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后,香港社會的動蕩和內亂局面得到有效遏制,但時下本土新冠疫情又讓香港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可以肯定,在香港與內地往來沒有恢復正常通關之前,香港經濟都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起色。
在香港與內地往來沒有恢復正常通關之前,香港經濟很難有起色。
其實,即便香港與內地恢復了正常通關,香港經濟也未必能夠很快煥然一新,因為香港經濟本身存在著許多令人擔心的隱患。首先,香港經濟結構過于單一和老化,占90%以上的傳統服務業很容易受到外圍環境的沖擊和影響;第二,香港人口嚴重老化,勞動力結構嚴重失衡,低技能勞動人口太多,而高技能勞動力嚴重匱乏,完全不能夠適應經濟變革的需要;第三,香港創新產業、科技產業、先導產業幾乎空白,令到香港經濟無法轉型升級,只能眼望著競爭對手一個個超越自己;第四,香港沒有善用好“一國兩制”優勢,相反,“兩制”還一直被一些反中亂港勢力當作阻礙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的借口,也令到許多香港市民誤以為,拒絕或者減少與內地合作才能夠保留香港特色,等等。
從香港過去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來看,以上種種問題如果不能夠切實得到有效改善和解決,那么,香港經濟前景堪憂,老牛拉破車式或蝸牛式的發展狀況仍然會一直困擾香港。然而,如果香港仍在以往傳統的發展思路框框里打轉,上述問題也是無法解決的,香港經濟要尋求新的突破可能性極小。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經濟體,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更是中國經濟輻射全球的高地,香港只有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并以此融入到國家發展的大局之中,才能破解香港所面臨的系列困境和難題,才能尋找到新的發展市場和空間,香港的優勢和特色才能夠得到充分彰顯和展示,所以說,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迫在眉睫,否則只能是坐困愁城。
香港需要轉變三大不合時宜舊思維
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自此,整個大灣區發展進入了熱火朝天的大發展新階段。正如規劃綱要所界定的時間表,到2035年整個大灣區規劃藍圖將全面實現,因此,時間無論對于所有9+2大灣區成員抑或對有意進入大灣區發展的企業、投資者和個人,都是一個時不我待的事情。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但總體上來說,大灣區的建設推進并沒有受到大的影響,即使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也于去年九月份就與內地實現了正常通關,人員往來完全恢復正常,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各項工作有序推進。現在來看,唯獨香港因為疫情沒完沒了,至今不能夠與內地實現正常通關,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工作也受到影響和延遲。
國家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實最利好的還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試想,到2035年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將有近一億人口的規模,人均GDP如果按照6萬美元的水平計算,那么,屆時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將有近六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整個大灣區不僅是中國最發達的高端制造業中心、科技研發中心、創新創業高地、商業貿易中心、消費時尚中心、海陸空交通樞紐,而且也將是世界經濟規模最大的經濟灣區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區,也將是中國國內經濟大循環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結合部以及中國經濟輻射全球的核心區域。這樣一塊巨大的市場蛋糕,就擺在了香港和澳門的眼前。
多數香港市民還帶著十幾年前的觀念看內地。
然而,香港最終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成果,還得取決于香港本身如何作為。坦率指出,香港社會上上下下的發展思維還沒有跟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步伐,多數香港市民還帶著十幾年前的觀念看內地,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性以及所帶來的巨大商機認識不足,需要轉變舊思維,提高發展認識。
首先,香港要摒棄邊境地區即偏遠落后地區不宜發展的舊思維。以前,香港都把與深圳交界的地區作為偏遠落后地區,甚至作為禁區,香港的發展規劃也從來沒有考慮到這些地區,相反,香港往往把垃圾填埋場、廢舊品處理等設施安排在港深邊界一帶。香港的這些做法不僅完全沒有顧及到鄰居深圳的感受,而且與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大局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格局的背景之下,以往與深圳交界的所謂偏遠地區如今都是香港最具發展潛力的新經濟增長點,是與深圳和整個大灣區進行實質性合作發展的寶貴區域。如果不轉變思維,仍然把與深圳交界的地區當作偏遠地區,不規劃,不發展,不合作,那么,香港后續發展將失去土地供應來源,香港發展的空間就將遭遇天花板,尤其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將會失去很多具體抓手和平臺,最終有可能淪為紙上談兵。
其次,香港必須摒棄以我為中心的單贏思維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舊觀念。無論對于國家、單位抑或個人,只有抱持合作各方都能夠分享到好處的雙贏或多贏思維,大家的合作才能夠長久進行下去。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其實本質上也是一種區域間的合作,然而,從過去香港與大灣區各地之間的往來看,香港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別人的利益的思維一直為人詬病,而且最終香港自己也沒有得到好處,甚至得到非常深刻的教訓。
譬如,為了爭取香港自身利益最大化,港珠澳大橋的設計建設在香港方面的要求之下被建成了單Y格局,如今行駛在大橋上的車輛寥寥無幾,不僅上千億的投資回收無望,甚至連部分銀行貸款的利息都還不上,大橋幾乎成了擺設;再譬如,香港的科技園和數碼港建設本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維全由香港本地公司開發,結果導致香港的科技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白白耽誤了二十多年大好時光。
港珠澳大橋的設計建設在香港方面的要求之下被建成了單Y格局,如今行駛在大橋上的車輛寥寥無幾。
必須看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9+2個城市和地區,各自都有自己的優勢和不足,只有攜手合作,各取所長,優勢互補,才能夠實現多贏共進的局面。如果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及別人的利益和長遠利益,那么,港珠澳大橋和香港數碼港的結局還會不斷上演,吃虧的還是香港自己。
再次,香港必須摒棄消極等待的思維,必須積極主動有所作為。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關愛有加,送了很多政策大禮給香港,對此,香港社會已經習以為常。其實,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推出中央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為港澳未來發展提供新的機遇和空間,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港澳發展與繁榮穩定的重大支持。然而,與以往中央送政策大禮包不同,香港要分享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成果,必須積極作為,主動參與其中,否則,如果消極等待,即便送到眼前的大餅也有可能吃不到。對于如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香港目前進展有限,還看不到有什么實質性成果,需要加油再加油!
香港需發力建設綠色金融中心
綠色金融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一個新方向。
2016年5月24日,香港金融發展局發表了題為《發展香港成為區域綠色金融中心》的報告,建議推動香港發展為區內領先的綠色金融及投資中心,并成立綠色金融咨詢委員會或同類機構,以制定長遠工作重點及提供協助,向本地和環球金融業傳達清晰明確的訊息。
2018年9月21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出席香港綠色金融協會成立大會時表示,香港正在發展成綠色金融中心,隨著內地對綠色金融及資金需求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相信能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務并捕捉相關機遇。2019年1月14日,林鄭月娥在第12屆亞洲金融論壇致詞時指出,香港政府致力于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能夠成為綠色金融和綠色融資的平臺和樞紐,第一只綠色債券馬上就會推出,將會撬動1000億港元左右的資金池。
令人遺憾的是,或許是因為2019年6月份以來香港社會動亂不止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等原因,此后,香港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的進展就沒有下文了,而港人聽到的卻是上海宣布將建設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消息。
不久前,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在談及上海未來發展時表示,要把碳金融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全國碳交易市場為基礎,打造國際碳金融中心。本來,香港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可謂先聲奪人,但兩年時間過去,上海明顯后來居上,如果香港自甘落后,那么,香港金融業又將錯失一次重大發展機遇。
眾所周知,中國已經全面邁上了綠色發展之路,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有專家指出,由于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任務十分艱巨,今后必須從以下五個方面發力:一是開發低碳能源,二是工業企業低碳轉型,三是生活用能低碳轉型,四是交通出行低碳轉型,五是吸收難以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由此,將會衍生出能源生產領域的新技術、新業態、新領域,與此同時,能源消費也將出現重大轉型。
可以預期,未來十年甚至四十年時間內,從供給側角度來看,風能、太陽能、地熱、水能、核電等綠色清潔能源產業將迎來巨大發展機遇,而傳統的石油、煤炭產業將逐漸轉型升級并壓縮生產規模;從消費側角度來看,綠色環保住宅和家居用品、節能空調、電動汽車等產品需求也將迎來大爆發。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總的投資規模將數以百萬億計,除了政府的部分引導性資金投資外,絕大部分必須通過市場進行融資,其中包含的綠色金融規模龐大。
正是在國家全面推動綠色發展轉型的大背景之下,上海提出要將“綠色”打造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新的名片。基于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求,上海提出將努力打造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綠色金融樞紐。依托上海的金融優勢,在支持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發展碳金融業務的同時,上海將進一步形成多層次的綠色金融組織機構體系、多元化的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多渠道的綠色產融結合和產業轉型的市場平臺體系。同時支持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申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推動區域和國際合作,有序推進綠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
其實,中國之大,完全能夠容納得下兩個國際性綠色金融中心,上海依托長三角經濟圈,香港則可依托大灣區經濟圈,只要香港緊跟國家綠色發展步伐,積極發揮自身金融優勢,綠色金融一定能夠成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新的增長點和亮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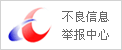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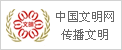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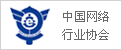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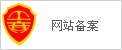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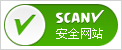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3-2022 Brand food.c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3-2022 Brand food.cn All Rights Reserved.